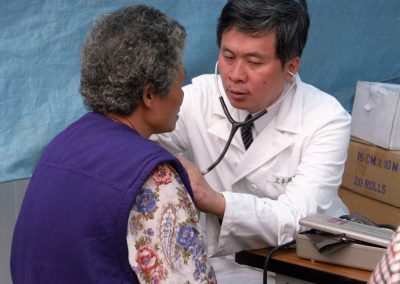我聽爸爸告訴我,他二十幾歲時,剛好碰到二次世界大戰(1937~1945年)的前段,那時臺灣人吃的米飯都要配給,農村的經濟落後,我們雖然是佃農[1],但自己種的米卻不能吃。
我是1949年(民國38年)生於南投埔里務農的家庭,家中九個兄弟姊妹(三女、六男),我排行第七。兄弟姊妹多,我們從小是窮怕了,所以大家長大後,開始賺錢時,第一個就是積蓄財產;不是錢,財產是不動產。我們兄弟每個人的目標,就是希望幾年內可以買田地、買房子。
1971年以後,買一甲的土地,可能沒有買一間房子增值得快。從我高職畢業,當兵、退伍後開始工作,曾做過林業領班,後來應父親召喚,回家跟著兄弟一起種木瓜,做起職業瓜農。上班也好、作農也好,我一有賺錢就不怎麼買土地,偏喜歡買房子,因為房子增值快,而且我們兄弟對於購屋投資都很有興趣。
1976年我經由爸、媽的朋友作媒,與黃瑞年結婚,婚後育有三個女兒;日子在農忙生活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凡無奇。
花蓮之旅 震撼發願
我弟弟就住在我家對面,弟弟的岳母楊木香是慈濟委員,時常來找他收功德款,我太太也跟著每月繳三百元,就這樣成為慈濟會員。1991年有一天,親家母因為大陸華東水災,來向女婿募款,說:「師父要救大陸,你趕緊捐一些錢。」平時弟弟對岳母很好,這一天手上正忙著把木瓜裝箱,直接回說:「啊!無閒啦!(臺語,音讀bô-îng,沒空、忙碌之意)」我剛好在場看在眼裡,想給老人家臺階下,於是向太太說:「去拿一千塊錢給親家母。」從此,親家母覺得女婿難度,度我好像比較快。
隔年,親家母來家裡問我:「你捐款那麼久,要不要去花蓮看看?」我本來想一個月才捐三百元,要去了解什麼?但又想到正好可以去花蓮做木瓜市場調查,於是就答應了她。當時很多人都搭慈濟列車到花蓮慈濟參訪,因為埔里沒有火車,所以是搭遊覽車去。
1992年5月17日,遊覽車從埔里開往花蓮,費時大半天,一路上,車中播放「幸福人生講座」的錄影帶,剛開始我沒有注意看,只是一路上聽著、聽著,我覺得聽這位師父講的和我在其他寺院聽到的不太一樣。埔里是個佛教修行道場密度很高的鄉鎮,平時我也接觸過一些出家師父,但錄影帶中的師父,不是講經,卻說要如何將一念悲心落實生活來幫助人,聽起來感覺有些契合我對人生的看法。
遊覽車抵達花蓮時已近傍晚,我們不是去風景區,而是先參觀慈濟醫院。隔天清晨五點多進到靜思精舍,在大殿後方的中庭,在搭採光罩的戶外空間下,有一位來自臺北的紀靜暘在分享,我看見證嚴上人,那時是坐在一旁破舊的藤椅上打著點滴。一會兒,上人對眾開示:「我昨天晚上很痛,痛到跟佛陀祈求可不可以分期付款,讓我今天能跟大家見面。」原來上人罹患帶狀皰疹,一整晚都痛到無法安眠。
就在那一刻,讓我心裡很震撼:「昨天參觀的醫院這麼大、這麼新,怎麼沒有讓師父去住VIP病房?怎麼沒有醫師、護士隨侍在側?」那一刻的感動,讓我在心中許下一個願:「如果我要走進佛門,就是這裡!」接著兩、三個月內,我兩度帶著全家人一起到精舍拜訪。
人少個案多 積極力邀鄉親入慈誠
回到埔里後,我就開始自動跟著資深志工一起訪貧;當時訪視的範圍包含整個南投縣,有些志工年紀大了,有些沒有交通工具,所以能進入山區看個案的人力有限。最多的時候我要負責兩、三百個新、舊個案,當時是抱著檔案在訪視,一次還接連跑了九天才看完。除了農忙之外,太太黃瑞年也會跟著我一起做慈濟,1994年我們同時受證為慈誠、委員。後來父親中風、母親臥病在床,需要我們兄弟輪流照顧,我和太太也沒有放棄做志工,只要時間排得出來,貨車開著就出門訪視或勘災。
1995年南投縣慈誠隊正式成立一小隊,當時只有七位慈誠師兄,我算是以最資淺的資格和經歷,於那年5月31日承擔小隊長。我認為既然要做,就做到最好。當時各區慈誠隊都要排班到臺中分會輪值值夜,才七個人如何擔得起來?迫於現實的壓力,我就開始積極招募師兄;不管是其他師姊的先生或環保志工等,只要有可能的對象,我就登門拜訪。我說:「你給我一個師兄,我還你一尊菩薩。」鼓勵太太們布施先生出來擔任護法金剛的使命。1995年9月,我開著車子穿梭南投縣各個村里;只要有希望的地方,我就前往介紹慈誠隊,回到家時往往是半夜兩、三點了。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在積極尋人和陪伴下,慈誠隊員快速地成長,至1997年,南投縣已有八十六位慈誠師兄了,並因此由一個小隊而茁壯為一個中隊,我擔起了中隊長的任務。所有的規模和成就,都是所有師兄背後努力付出的成果和累積,這些成績,絕不是一個人所能完成的。我兩年多的時間裡,共買了六十五條慈誠隊領帶與人結緣,期許他們戴上領帶後,可以擔起慈誠隊的責任!到1999年九二一之前,慈濟中區慈誠大隊第八中隊,包含埔里、草屯、南投(市)、竹山,以及彰化芬園一帶,慈誠中隊員有一百二十餘人。
臨危不亂 先安頓左鄰右舍
1999年9月4日為了援助土耳其和科索沃,全臺慈濟志工同步上街募款,我在貨車上裝了一組擴音器,是廣告用的那種有喇叭的麥克風,在路上巡迴廣播勸募。因為那時認識慈濟的人畢竟有限,上街頭募款,靜靜的行列不容易吸引店家出來,用廣播車引導,總是容易吸引住家的注意力。
誰都不會想到,9月21日發生大地震,那夜一陣天搖地動後,馬上就停電了。我和太太跑下樓,走到屋外,在我眼前是左鄰右舍的房子有的倒了,我住家附近的電視大樓(中投有限電視——埔里公司)倒塌後直接壓垮它後面的房子。我心中立即想:「這麼嚴重,鄰居、親戚朋友,有沒有怎樣?」
那天我兩部貨車沒有停進車庫,放在露天的停車位;我家附近有一塊大空地,還沒有建房子,我第一個動作就是先把貨車開到那塊空地上,把車燈打開,請住在對面的小弟管這部貨車的燈,在暗夜中為大家照明。
埔里那時候都用桶裝瓦斯,大家日常習慣就是打開以後就不關,包括洗澡的、廚房的,都沒有關。我想到家裡瓦斯不知道有沒有關,此時不能點蠟燭進去看,因為曾經有人點蠟燭進去看,發生爆炸了。趁著餘震不大,我溜進家裡去關緊瓦斯開關,也提醒左鄰右舍要關緊瓦斯。
我們夫妻倆分頭把左右鄰居叫出來集中到空地上,有些老人家沒有辦法快速地跑出來,出來的人就幫忙找。那時候餘震不斷,為了找附近鄰居,有餘震時就趕快跑出來,停了再跑進屋裡去,把左右鄰居、附近的親戚都叫過來集中在一起,點名後知道有人受傷,很萬幸的沒有人被壓死。那時,已經超過凌晨三點了,我想到師兄、師姊,不知有沒有怎樣?住最近的就是陳松齡和吳翠屏夫婦,他們年紀比較大,我開一部貨車去看看他們家,幸好他們一切無恙。
前往臺中求援 沿路慘不忍睹
安頓好鄰居親友,我們決定開車前往位於中正一路的埔里聯絡處。我住在建國路,離鎮上要道的中山路很近,車子一進到中山路,只見每一個十字路口的店面,幾乎都倒了,要從北環路轉也轉不出去,尤其中山路的幾棟大樓全部都垮在路上。
哇!這麼大的災,太嚴重啦!同時我也發現一個現象,聽不到任何救護車的聲音,也沒有消防隊的聲音。原來消防隊也被壓垮了!我開著車子走著、看著,知道有人受傷、有人往生了……
手機打不出去,電信都中斷。我本能反應要先到臺中求救!因為災難太大,我們救不完!我開車往臺中去,當車子出了愛蘭橋[2]的時候,看到很多往生者被抬出來放在路邊;到了柑仔林,快接近福龜附近,中潭公路整條斷斷裂裂地,車子沒有辦法開快。
快到柑林隧道的時候,又遇到一個大震,路旁的土石被震到掉下來。停下來不走會被壓到,前面是隧道,進去的話,會不會被困在隧道裡面?此時必須馬上抉擇,我告訴自己:「趕快進去吧!至少不是馬上被壓死。」當時幸好安全穿過隧道。現在回想起來若是進隧道被壓死,不就連身體都找不到嗎?
過了柑林隧道,到了福龜,災情更嚴重,死的人整列地排在路邊,沒有白布可以蓋,全部用三合板或鐵片擺著,就是地下墊一個、上面墊一個;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一路上就看到死了很多人。到福龜,天已經露出魚肚白了,我們遠遠地就看到「九九峰」山頭所有的草木全部都滑下來,一片光禿禿的。在那一點點光線之下,大地顯得一片死寂,看起來真像是世界末日。
為了到臺中求援,車子就只得一直往前開,開到藝術村加油站,看到加油站已經動用他們自己的汽油發電機。我停車問一位員工:「你們這邊的電話還能不能打?」他跟我說:「剛才還有打電話回報總公司,辦公室那支電話還沒有斷,你可以打。」所以我一進去就先打給臺中分會。
我電話一打通,就跟分會總機說能不能請「大咖」的人來聽啊!剛好蕭惠特師兄在電話旁邊,我跟他說:「這次地震,埔里非常嚴重,你們若要進來,要想辦法調底盤比較高的車子,不要用轎車,因為路況很不好。」蕭惠特回說:「臺中也一樣這麼嚴重啊!」他說臺中已經開始動員救災,那時大約清晨四點多。
通訊交通斷 心掛法親不畏難
當他跟我講完,掛了電話以後,我不知道為什麼靈光一閃,竟然記起 「03-8266779」那支電話的號碼。因為以前很少跟精舍聯繫,那時我就強迫自己撥過去。撥通以後,我就跟總機的師父說:「師父,我們埔里已經變成土耳其[3]了。」講到這裡,再一震,電話斷了,就再也撥不出去了。
臺中無法去了,我就開車到草屯去找簡棋煌[4],我們直接到他家,看到房子沒有倒,他人不在,跑出去了。還看到他家旁邊的房子是向上隆起,而且二樓壓到騎樓。一時找不到簡棋煌,我就轉去找曾明松(草屯區慈誠隊員),我們一起去訪查草屯區所有慈誠師兄的災況,還好,都沒有傷亡,我心中感到比較安心,至於其他慈濟人的情況,就請他們就近了解。
我和瑞年打算轉往中興新村,但中興新村已經沒有辦法開過去。於是轉去南投(市),因為南投(市)也有很多位師兄,到了南投(市)的軍功橋[5],橋頭斷了,對面的南投酒廠爆炸起火了,車子過不去。那時南投(市)各區慈誠師兄的主要聯絡窗口,草屯有簡棋煌、南投有曹永東、竹山有莊正飛,既然出了埔里,想一一把他們找出來,確立自己人的受災情況。結果路不通,沒有辦法再進到市內去。
此時是早上五點多,我才想到我的孩子在哪裡?我趕快轉往彰化去老么她就讀的學校。到彰化的時候,手機訊號就通了,老么已經跑去投靠臺中的大姊,她大姊那時就讀東海大學。我告訴她現在災況很亂,暫時不要回來埔里。知道老大、老么兩個孩子平安,我們就打算回埔里。
在回埔里前,我想起住在魚池鄉的達宏師父[6],他的「寂照蘭若」即將落成。他一個人孤單地住在那裡,先去看他是否平安,所以我轉往魚池先去看達宏師父。幸好他的房子好好的,但也有很多東西倒了。告別了師父,回到埔里聯絡處,已經下午一點多了。
廣播繞行 提供救援資訊慰鄉親
從凌晨三點多,開車從埔里、草屯、南投(市)、彰化再到魚池繞了一大圈,回到埔里聯絡處的時候,已經有外地的師兄進來協助救災,當天埔里的師兄、師姊動作也很快,早上六點半就開始煮稀飯給鄉親吃。
我們開始張羅緊急救災,發現到幾個嚴重的問題有待解決,當天晚上災民已經沒有地方住了,即使有房子,因為餘震不斷,很多人也不敢再進去住。最嚴重的就是沒有廁所,也沒有水,因此埔里聯絡處一樓的廁所都已經滿出來,連要洗廁所都沒有水。還有救災要煮東西,家裡能夠搬出來的瓦斯,通通都號召搬出來了。所有師兄、師姊都出來救災,從白天一直做到凌晨三點(9/22),已經疲累到受不了;當大家都回去休息,我和瑞年兩個人若也走,聯絡處就沒人留守。所以當晚我就把車子開到聯絡處旁邊的樹下,想說可以睡一下,沒想到才剛睡下去,就有受災民眾來到聯絡處求援。
很多人沒有經歷過災難,受到驚嚇後晚上睡不著,肚子餓沒有東西吃,也買不到,他們白天在慈濟有飯可以吃,所以才凌晨三點半就有人來問:「你們這邊有飯可以吃嗎?」瑞年就起來把稀飯熱一熱讓他們吃。
這就讓我想到了,怎麼樣才能讓受災民眾知道慈濟有救災資源,大家都沒有經過那麼大的災難,比較遠的地方怎麼會知道?我想起為土耳其地震募款時,用的麥克風(擴音器)事後就擺在家裡,我趕回家去把它拿出來。地震後第二天(9/22),一整天我開車在全埔里鎮跑,一直跑、一直廣播。我廣播主要兩件事情:第一哪個地方有飯吃,第二哪裡有醫療服務站。
那時候不單是埔里聯絡處有提供熱食,還有很多臨時服務站都有煮熱食。我家旁邊的空地,政府有用帆布搭了幾個可以遮風蔽雨的棚子,我把家裡的瓦斯桶搬過去,我們社區志工在那邊架起瓦斯爐,食物從聯絡處拿過來煮,蔡燕宗也在他們家附近煮熱食給鄉親吃。提供熱食卻另外延伸沒有碗的問題,原本我們聯絡處備用的碗一下子就被拿完了,我在廣播的時候就順便告訴鄉親:「不管你們到哪個地方去吃飯,希望都要拿著家裡的電鍋內鍋、鐵鍋或其他鍋子,去盛回家吃。」
慈濟已經設有四個醫療站,埔里聯絡處、埔里基督教醫院、埔里高工、育英國小;不只是慈濟醫療體系,還有各方的醫療人員也都進來,雖然醫療設備還不是很齊全,但就是可以緊急搶救一下。只是很多人沒想到地震那麼嚴重,醫療人員一進來,大多無法馬上退場。所以我就廣播讓大家知道:「如果有需要,就到最近的醫療站看診,都不用錢。」
白天一直開車繞,一直廣播;到了晚上,我發現很多受災鄉親坐在家裡或在臨時帳篷裡有點兒恍神,因為大家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第三天,我同樣開車繞著全鎮,一直廣播,就想要給予受災鄉親一些心理建設。我告訴他們:「大家不要在家裡面憂心,是不是出去走走?看哪個地方有東西可以吃,哪個地方有醫療站。」然後也告訴他們哪個地方有物資可以拿,這些東西都不用錢。「我們大家互助合作,大家共同勉勵,大家共同來度過苦難的日子。」我就這樣反覆地說。
愛心物資 有需要的就給
各地物資湧入,另外一個問題出現了,就是我們缺乏人力來搬運。雖然鎮公所地震時倒了,但原地旁邊還是有人駐守,所以外面的物資進來會先送到埔里鎮公所,在那裡也設為臨時物資的集散中心。那時候路況很差,往往從外部送到埔里就已經是下午五點以後,人員幾乎都下班,就只留一個人駐守在那邊,物資送達後,公所的人就會說:「慈濟有在收啦!你們把物資載到那邊下啦!」因此,很多物資五點以後陸續下在埔里聯絡處,那誰來搬?誰來整理呢?師兄、師姊已經累了兩、三天了,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準備了慈濟志工的背心,只要有人來排隊拿物資的時候,我就說:「一個人穿一件背心,大家自助。等一下東西卸下來以後,幫忙把它排好,要拿東西的時候,你們就優先。」這樣帶動了許多受災民眾一起協助安置物資。
最大量的一次,就是上體下通法師[7]號召一家報社,送了十輛板車的礦泉水來。十輛板車的礦泉水,量很大,而且非常重;埔里國小後門圍牆邊排滿一整排的礦泉水,就是他們送來的。當時我就請要來領物資的民眾,協助把礦泉水放在圍牆邊,然後把它們排好。所以慈濟救災的第三天開始,礦泉水是免費讓人家搬的。有人來問,我們就說:「你們若需要水,那就隨意搬。你搬得動,就搬回家吧!」
其他物資也是一樣,人家要來領東西的,就請他們幫忙把東西整理好,然後告訴他們:「你們要回家的時候,每樣東西各拿一件。要睡袋你拿一個,要棉被你拿一條,要泡麵你拿一箱,要麵條你拿一包……」就唯一沒有帳篷,因為帳篷很快就沒了。
在物資發放當中,也發生一些爭執。因為埔里的師兄、師姊都沒有大型救災的經驗,當很多物資到的時候,有人會認為:「你來領東西,要不要登記?」有的人說要登記,有的人說不要登記。有人說:「你沒有登記的話,會養成他們的貪念,反而拿得越多……」
我認為這些物資都是人家自動拿過來的,不是慈濟去募來的,有些還是沒有地方下貨,然後送到慈濟這裡來的;他們會給慈濟,因為他們相信,慈濟會發出去。所以在那種情況下,我認為能夠發出去就發,不是把它放著,放著也沒有用啊!所以從第四天開始,我就把所有物資全部整合在埔里聯絡處前面,然後用桌子圍起來。鄉親從仁愛路走進來,從我的面前走過,然後從中正一路的小巷走出去。我們志工就告訴鄉親說:「每一樣東西,你手上帶得走的,只能帶一件。」
如果有人不夠,那就到後面再去排隊。要排隊,拿幾次,我都不管。因為那時候,仁愛路繞五圈,從頭排到尾,要兩個半小時以上,才能拿一次。在那種情形下,若說要登記,怎麼登記呢?而且我們又怎麼能夠去判斷誰多拿了,誰少拿了?
唯一有管制的是嬰兒特殊奶粉,嬰兒特殊奶粉很多志工都沒有辦法管,我就說:「那我來管。」我就把嬰兒特殊奶粉蓋起來,然後問來領的人:「你家是吃哪一個牌子的?」第一他要講得出牌子來,第二我翻開看,有,很簡單,就給一罐,就拿回去;沒有,就沒得給。救災奶粉,人家捐的多數是大孩子的奶粉,而小孩子的特殊奶粉是不能隨便吃的。因為我大女兒小時候就是必須吃特殊奶粉,所以我知道有差別性。因此,就只有這種特殊奶粉有管制,其他的物資都沒有管制。尤其那時的物資堆積如山,有人來領就給了。
第四天的物資發放,我把動線和數量分配整合好,就不再像第一天、第二天那樣不知如何掌控。白天人來人往,忙得天昏地暗,到了晚上,我就和瑞年守在埔里聯絡處,並用車子堵在路邊,有人要卸東西的時候,就由我去把關。因為有人送很多肉品,我們慈濟不能處理、不能接、不能發。我還告訴他們,慈濟什麼東西不能接,什麼東西可以接。
一天,不知道臺北哪個人在電視聽說「災區欠衣服」,所以埔里聯絡處被倒了堆積如山的衣服,大多是舊衣服。我認為這個要先帶走,因為衣服不可能在這個地方放那麼多。而且都是舊的,銷不出去。衣服的量有多少呢?後來拜託彰化區的志工來載,他們開了十輛回收的大卡車才全部載出去。
在這麼緊急救災當中,沈順從師兄與埔里國小協調,把禮堂借給慈濟置放堪用的救災物資。因當時埔里國小的禮堂沒有倒,而且剛好就在聯絡處的對面。那時多數是置放一些食品、內衣褲,還有簡單的救助物品。
堅持發帳篷 為鄉親擋風遮雨
第四天的發放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插曲,就是帳篷。宏碁公司用一輛板車卸下幾個棧板的帳篷,它是從泰國進口來的,可以住四人的帳篷,有四百六十多個。送到的時候已經晚上,大約九點鐘卸好貨。那天晚上已經吹起東北風了,天氣也開始下起毛毛雨。鎮上還有很多鄉親都沒有帳篷,有師兄就認為這個帳篷現在很珍貴,大家都很缺,所以必須要有證明是受災鄉親才可以領。
當時在現場有八十一位鄉親看到慈濟有來了帳篷,我的看法就不一樣,便跟當時接管帳篷的師兄說:「今天這個帳篷如果沒有發出去,明天可能會出問題。因為人家回去會說:『慈濟有帳篷,但沒有發。』而且這個帳篷他們很需要。」
眼見開始下雨了,讓我很堅決要「即時」發送帳篷。我就跟在現場的陳瑞成師兄和我太太說,趕緊開兩部車子過來:「你們把車子開過來,留下八十一個帳篷,其餘的,一車各裝一半。一車向南往河堤南路走,一車向北往和平東路外環走。只要你們看到有人睡在路邊卻沒有帳篷,就告訴他:『我們是慈濟,我們有帳篷,你要不要?』需要的話就馬上給一個。」所以他們就帶出去繞一圈,當然很快就把帳篷發完了。
同時,我就跟那八十一位鄉親說:「你們一個人先拿一個帳篷,但是大家暫時都不能走,因為我們必須把這些東西都載出去以後,你們才可以回家。否則你們回家一說慈濟有帳篷,若說成一千個,那我們實際沒有啊!就會暴動。」當載帳篷的車離開後,我就說:「這邊現在都沒有帳篷了,你們也都知道了。你們帶回去就自己用,但不要再告訴人家說慈濟還有帳篷。」
帳篷的事,就這樣解決了。當然有人會有意見,但是我認為:「在那個當下,不這樣處理,怕後續無法解決。」此外,慈濟留著帳篷或慢慢地發,而災民卻在淋雨,情何以堪呢?所以當時我也不顧反對意見,就堅決地這樣處理了。第五天,埔里聯絡處照常發放物資、煮熱食供應,晚上我和瑞年一樣守著聯絡處。
挨家挨戶訪視 發放急難救助
在救災的同時,中區志工林雪珠等人進來埔里支援訪視,他們是帶著救災的錢進來的。大家分配路線後,由埔里當地的志工帶路,兩個或三個人一組,一邊訪視關懷,一邊發放急難救助金,同時也造冊登記受災情況。最主要就是鎮公所倒了,民政課剛好在一樓就壓在底下,他們也沒有什麼名冊可以提供,所以全部都是憑著志工的經驗去把它處理到最好。
我也有自己的訪視路線,訪視的範圍是蜈蚣里那一帶,我的方式是:「死亡的馬上給救助金;房子倒的,暫時沒有給;就是傷亡的先做。」像賀伯風災(1996年)救災的時候,上人都親自指揮或親自到災區。他給我們一個觀念:「救災不是救貧,救災要及時;要救,就要一次救到活。」
這是為什麼我什麼東西都發得出去,不要只給一點 點,該給的就給。因為物資是大家捐的,有時效性,當時不發,以後就沒有用了;再者,災民有需要就給吧!一次把他救到活。那是上人在賀伯風災時教導我們的觀念──要救,就一次救到活。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他兩個兄弟分家的時候,分到舊式的三合院。他年紀很大才生了兩個兒子,娶了媳婦以後,他把客廳的兩邊用夯土加蓋兩側的廂房給兒子媳婦住。其中一個媳婦生兩個孩子,一個生一個孩子。結果地震的時候,他客廳旁邊的夯土牆就往兩邊倒。我朋友那一家同時死了五個人,就是三個孫子、兩個媳婦同時往生了。
我去送慰問金的時候,朋友帶我去翻那個冰櫃,因為還沒恢復電力,那時是用發電機的冰櫃。他說:「忠厚啊!你來看,我的兩個媳婦啊……」我看到在冰箱裡的孩子還很小,他媳婦死在裡面,是一邊各抱一個孩子……那種情境,情何以堪啊!
在訪視當中,我看到很多傷亡人家的房子,地震來時,不是上面塌下來,而是女兒牆先垮下來。雖然現在沒有夯土的房子,但是常常在樓下的樓梯旁邊,建一個女兒牆,因為它沒有用RC(鋼筋混凝土)連著,就直接用磚牆扶著這樣蓋下來。人是脆弱的,不需要多少斤,兩百斤就把人壓扁,不是壓死而已,而是壓扁。所以,我後來在重建住家的時候,就全部一體成型,整個鋼筋全部連起來。
見上人親臨 弟子釋放傷痛
9月25日中午前,上人從臺中進來南投勘災,一路到了埔里,在進聯絡處之前,他已經先到埔里鎮市區繞了一圈才進來。見到上人,弟子們難掩悲傷的情緒,有人掩面而泣,有人默默拭淚,有人轉憂為喜……千頭萬緒,總是覺得「終於,上人到了!」多日來,心中的壓抑好像找到了釋放的缺口。
上人一進來先看到熱食區與發放區,他巡視煮熱食的情況,那時候師姊都煮羹飯,飯比較單純,但羹是熱騰騰地在冒煙。師姊們從早煮到晚沒有停,一鍋接一鍋,已經連續煮了五天,大家都累到兩眼發紅。羹很大桶,一抬起來是四、五十斤重,上人站在旁邊看了就說:「這樣很危險!」他怕大家在筋疲力盡的時候,若一個倒下去,就不得了了。所以上人說:「如果有別人是專業在煮的,我們就放出去,讓人家煮。」救災初始,國軍弟兄也是有來吃慈濟志工煮的熱食,等到他們正式在組合屋那邊下營,慈濟就把煮熱食的工作交出去。因為國軍一出來,他們就有設備齊全的炊具,比我們臨時找來的鍋灶還好用。而且,我們的志工也多數是災民,師兄、師姊的壓力已經夠大了,何況當時埔里聯絡處沒有正式的廚房,就只在廣場上架起一個個的鍋爐來煮;所以,該放的時候,就放給別人做。
為了廚房的事情,很多師姊向上人建議:「是不是先建一個廚房?」包括沈順從師兄也附議要建廚房,但我都沒有講話。上人把我和沈師兄兩個人叫到牆角邊去,上人第一句話就說:「你們兩個不要常常爭吵,要『和』一點。」因為我們會為了發放物資要不要登記、要不要限制……意見不同,就吵起來了。當時的埔里聯絡處,只是一個只能容納百人以內的共修處,還不是正式的聯絡處。在那種兵荒馬亂的時空下,沒有正式的聯絡處,卻要先建一個廚房,是一件顛倒的事。所以上人一直都沒有答應,也沒有表示意見,他聽到最後,就問我:「陳居士!你的意見怎麼樣?」
我跟上人報告:「其實像這種天災很少,不見得會常常有。先有正式聯絡處,就會有廚房;沒有正式聯絡處,不用先建廚房。尤其我們在救災的時候,救災可能幾天而已,那就饅頭吃一吃,開水配一配就好了;吃的問題,應該沒有那麼嚴重啦!」
上人就跟我和沈師兄兩個人說:「對啦!我們做慈濟,不要那麼看重吃的事情。」聽了上人這麼說,從那個時候開始,每一餐不管飯碗大小,我都只盛一次飯。就是想著上人所說的:「不要那麼重視吃的事。」也因為這樣一段過程,舊的鐵皮廚房就留著繼續使用,直到八年後(2007年)佛堂蓋起來以後,埔里聯絡處才有了正式的廚房。
一碗分四碗 再苦有師父陪你
上人來到埔里聯絡處時,我排在發放最前面,上人直接在我的面前下車。他一下車看到我,就跟我說了一句話:「你這樣發物資,是對的。」我當時沒有反應過來,後來我才意會到,一定有人跟上人報告:「陳忠厚在埔里發物資、發帳篷,都沒有登記,都沒有做紀錄,直接就把物資發出去。」
很多人認為大災難的救助,應當要記錄我們發了多少?什麼東西發多少件?發給誰?要一一記錄。」但我認為,在那個當下,如果樣樣事情都要這樣做,除了沒有效率外,來領東西的人,他們從來沒有遇過這麼大的災難,會對我們不諒解。所以我決定不登記,讓大家需要的就拿走,不去考核人家有沒有重複拿。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帳篷的事,是沒有人重複拿,因為一次發出去就沒了。
上人那一天來了以後,就給弟子們很多的慈示與關懷,也肯定志工這些天的救災模式。而那天,卻是我在做慈濟的生命裡,一個最重要的轉捩點。上人要我帶路到埔里國小去看存放的救災物資。當我們一行人走過了圍牆,看到整個埔里國小校舍都倒了,我站在上人旁邊,其他都是隨師的,上人跟我說:「在外國,社區的學校是救災的中心。那麼,你們這一次在災區,所有的學校都倒了。如果以後我們有因緣幫他們建學校,我們要把它建成千秋百世都不倒的救災中心。」那一刻,我見識到大修行者的大悲心。我知道,上人已經萌起了要建「希望工程學校」的念頭。
那天中午午齋的時候,上人給我「一碗師公飯」[8]的啟示。就是那天中午十一點多,我在廣場發放時,上人要我一起進屋用午餐。我拿著環保碗上樓時心想:「師父很疼我,知道九二一我們每天吃羹飯,他一定從臺中帶很多好吃的東西來慰勞大家。」上二樓後,我以為有很多人,結果只有上人跟兩位精舍師父。一位師父從一個灰色的環保袋裡面端出一個大碗公,上面蓋著一層保鮮膜,裡面只有一碗「師公飯」。
精舍師父把那一碗師公飯分成四碗,因為我帶的環保碗比較大,就分最多。每個人分一碗,上人只分半碗。然後從頭到尾,上人只講:「我們來吃飯。」沒有再講第二句話,四個人坐在那邊默默地把那一碗飯吃完。
我在上人面前,忍住所有的眼淚。那一刻,其實我內心非常明白,上人要告訴我:「無論你多辛苦,都有師父陪你走過去,即使只有吃師公飯也一樣。」這也是影響我做慈濟後半段這二十年來的核心精神。
用完餐要下樓時,上人跟我說:「你等一下跟我去看一個地方,要建救災的大愛屋,你跟我去量一量。」跟在上人後面,我站在埔里聯絡處二樓的樓梯口上,我往下望,上人那一襲長袍灰衣襯托下的背影,消瘦的肩膀,我看到他必須擔起全天下眾生的沉重負擔。當下,我再也沒辦法忍住眼淚。我在內心告訴自己:「無論怎麼樣,都要幫上人分擔,即使剩下一碗師公飯,自己也要甘願承擔下來。」
災民非難民 救災屋非難民營
然後,我就和上人、林碧玉副總去看地,就是信義路[9]那一塊臺糖地,有三甲多。還沒有地震以前,那是我想要標來種木瓜的地方,因為那塊地四四方方,又有水源;它的面積多少,我都很清楚。
去了以後,上人就說:「你等一下去把它量一量,看看全部多少,然後傳給我,我們要準備在這邊蓋房子。」我跟上人說,那個地方我太熟悉了。我就說:「那塊地,若像建工寮一樣,把它建成十寮;一寮一百間,剛好可以建一千間。」
上人看著我,看了很久,然後說:「他們是災民,不是難民。你說的那種,以後會變成難民營。」我又跟上人說:「救災階段的房子,這樣連過去一百間最快。鐵架一直架過去就蓋好了。」上人很耐心地跟我解釋:「我們蓋給人家的,都有規定的坪數。如果你把它連在一起,戶與戶之間沒有空間,很快左右鄰居的孩子就吵架。」他又跟我強調說:「他們是災民,不是難民。我們要蓋的是那種有尊嚴、有隱私的救災屋,而不是難民營。」
那時候我對雙併的、別墅型的房子沒有什麼概念,上人說:「你找人把土地的尺寸量起來,然後傳給我。」我回答說:「師父,我等一下回去找我師姊來,尺寸量一量,我就傳給您。」
上人又看著我說:「在這種救災的時候,你不要每件事情都自己做,要把所有的事情分給大家來做,不是你一個人攬著做。」
我永遠記憶深刻,上人到埔里救災的第一天,真的是從頭教我教到尾,重的話、輕的話,該講的話,都直接講了。從那天早上十點多到下午兩點多離開,我一直都跟著隨師團隊在走。那一天對我來講,是做慈濟七、八年來,整個生命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危機即轉機 助他人也幫己
自從上人來了以後,埔里的師兄、師姊就有目標了。緊急救災階段過後,接下來就是建大愛村。位於信義路的大愛一村是當時規模最大的,共有三百二十戶,後來還有西安路上專為原住民建的大愛二村,也有一百零六戶。其實在跟鎮公所等相關單位談埔里組合屋的時候,南投(市)中興新村就已經動工了。
蓋大愛村,來自全臺各地支援的人非常多,就產生「吃飯」的問題,因為很難統計。尤其是星期六、星期日,或者放假的日子,有多少志工要來幫忙?可能當天才知道人數,所以「煮飯」就變成埔里志工的夢魘。
剛開始的午餐,由外縣市志工來支援,到後來他們就進到埔里住。每個地方來輪流做三天香積,但是善後的部分,還有生活茶水是由埔里志工來做。這就衍生另外一個問題:「我們自己的家破碎了,還有很多事情要善後,沒有人怎麼辦?」沒有人,就要找人啊!於是社區志工開始產生了。
我們去找可以來幫忙的人,地震以後很多人沒有工作可以做,把他們請來後就告訴他們:「你就來這邊吃飯、煮飯、揀菜、洗碗、做功德等等。」像陳炎麗、胡瓊丰師姊,她們也是那時候找過來幫忙,後來成為慈濟委員的。因為外邊來支援的人總是有限,就這樣,埔里社區志工的人數,就有明顯的成長。
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
建大愛村需要採買很多小零件,埔里大家都受災,都需要採買重建的工具,所以很多五金行沒有辦法讓慈濟簽帳,而是要現金。那時我擔負起採買的任務,欠幾個螺絲、欠幾條皮帶、欠幾支掃帚等,都要去張羅,但我一個人又裡又外,就請志工去買。當時埔里人沒有習慣開正式的發票,所以開出來的發票就隨便寫個「慈濟會」、「慈濟功德會」……然後晚上我回到工地,會計一看到就說:「陳師兄!這疊你拿去換。」剛開始是連這種「發票不會開」的事情都發生。因為埔里小,鄉下誰管你一定要寫十五個字的「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所以換發票這種小事,都要一個專門的人去處理。
這當中,有一家五金行(現名:國棟五金有限公司),他們主動跟慈濟聯繫,從建組合屋到希望工程期間,讓慈濟志工隨時都可以簽帳。所以九二一過後,他們成了埔里第一大家的五金行。想想,慈濟的希望工程那麼多間、組合屋規模那麼大,而且這種善的循環大家會看到,都跑到那家去買,所以他們就變成了生意最好的一家。
領補助或住組合屋 抉擇難取捨
組合屋建好了以後,牽涉到一個問題是誰進去住?當時九二一救災的條例中有一條是房屋倒了以後,政府會給二十萬,但是給組合屋的時候,那二十萬要放棄。組合屋可以住到重建完畢,那時候估計是兩年,後來延到三年,其實全部遷走大約三年多。
本來馬上可以領二十萬,但是進到了組合屋就不能領,這是人性的考驗。那個時候要說服有這種想法的人才是困難,因為有人會想說是不是去領二十萬,然後另外找一個人的名字去住組合屋。但這對很多人就不公平,所以在那當中就折衝很久,後來由政府(鎮公所)出證明,即「放棄不領」的證明。因此,組合屋是跟政府合作,他們不領二十萬的救濟金,才能撥給他一間組合屋。
大愛村的房子蓋得很快,還未過年受災鄉親就已經搬進去了;住進去以後,因為房子比預期的好很多,產生很多善的循環,像陳秋甘、潘麗娘師姊也是因為住進大愛村,後來受證成為慈濟委員。大愛村是一個善的居住環境,幫助非常多人,但是時間一到,搬離開大愛村後,有些受災鄉親,經濟生活上仍有問題,因為地震後百業蕭條,有些人的家到現在一直沒有重建。
包括我自己也曾住進志工區的大愛屋[10],我曾想過,如果那時候組合屋不是建在公共的土地上,而是把它建在我家的土地上,甚至我吸收那些建材,那麼我們就不必離開。這樣,地震以後我重建的路程會順很多,因為我自己有土地。尤其在埔里鎮住進組合屋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有自己的土地。那些建材以後都不用拆掉,可以讓人住個三年、五年,如果保養得好,可能到現在都還不會壞掉;我在重建的過程裡面,就不必那麼急迫。當然現實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到了莫拉克風災,慈濟所建的永久屋就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就不用再轉移一次。因為臺灣有一句俗諺,叫做「一年移栽,三年枯黃(臺語)」。就是說,你只要換一個環境,可能需要用三年的時間才能修復,才能重新再開始。
希望工程 地湧菩薩善效應
組合屋完成了,接著就是希望工程。認養援建希望工程學校是上人不忍孩子教育受中斷,因為教育是人生的希望,也是社會下一代的希望。但希望工程的援建也是讓埔里慈濟志工人數得以倍增的重要一環。
埔里鎮上有七所希望工程學校,埔里國中、國小,大成國中、國小,中峰國小、溪南國小、桃源國小。除了溪南國小和桃源國小,其他五所都是埔里鎮上的大學校,大學校就變成了所有埔里社會中堅分子,像二、三十歲、三、四十歲的家長,他們國中的孩子、國小的孩子必須面臨馬上沒有學校就讀的窘境,但慈濟在很快的兩年裡面讓學校全部落成。
在重建的過程中,動用很多志工,包括校園景觀、鋪連鎖磚,還有香積的支援。兩年裡面,善的循環,讓很多家庭知道慈濟在做什麼,希望工程援建帶給社區重大的影響;因此,希望工程全部完工以後,慈濟埔里的志工人力倍增。
地震後遺症 百業蕭條難復原
九二一地震時,除了我三哥的房子沒有倒以外,其他三個兄弟倒了七間,我自己倒了四間,包括爸爸留下來給我的祖厝也全倒了。兄弟中,我受災最嚴重,因為我買最多的是房產。我認為在高經濟時機,很多人用槓桿原理去買房,就可以賺到錢,當時貸款買房子,往往有一塊就貸九塊。買的是預售屋,在建造完工時幾乎就賺一倍了。
地震後,房屋全倒當時一戶補助二十萬,而且要把房子全部挖掉[11];如果選擇住進組合屋就沒有全倒補助金。土地如果是自己的,房子挖掉至少還留下一塊土地,但我買的都是大樓公寓,土地是共同持分,不是個人的。此外,建商很會精打細算,地震前購屋是三百多萬的房子,重建時,一戶就漲到七、八百萬。在這種情形下,很多受災戶都沒有辦法再買回來,只好放棄。選擇放棄,就只剩權利金;尤其大樓土地的持分很少,權利金當然少,只有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左右。我不得不選擇放棄,但以前的貸款還是要繼續繳納。
受災已經沒有錢了,房子都倒了,經濟上又因地震效應,賺錢比較少;還有三個孩子的教育費,當時兩個在上大學、一個讀高中,加上不得不展開的重建經費等等,一連串的事件,對我都是極大的壓力。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中,其中有一條就是「貸款可以慢六年再繳」[12],但沒有說這六年的利息是免掉的。因為我是向銀行貸款,銀行就把那六年的利息累積,加到本金。六年後,我本來欠的不是那麼多,再加上六年的利息,那就雪上加霜了。
房子要重建、孩子讀書剛開學要學費,加上地震讓市場蕭條、水果價下跌……我是種水果、賣水果的,生活等各方面的衝擊,一時沒有辦法把經濟拚起來,那種千辛萬苦,實在很難言喻。最慘的時候是三個孩子全部都在讀大學,私立大學學費,加上在外地的生活費,當父母的只能咬緊牙關,為著拚新臺幣而努力。
每天早上一睡醒來,就想「什麼時候要繳哪一條錢?什麼時候孩子會打電話回來?什麼時候要重建?……」幸好以前我們有賺些錢的時候,並沒有亂花。雖然貸款買很多房子,但是我們謀生該有的機器設備都有,所以九二一地震之後那幾年就開始消耗以前的老本,包括把一些保險全部解約換現金,儘管中途解約不划算,但總是可以換現金回來用。
更嚴重的是,地震以後,房子沒了,要拿什麼東西去借錢?土地很少,借不了錢。而我最多的土地是農地,農地除了農民銀行以外,有些銀行根本就不放款。諸如上面的種種原因,我拖到第十九年才把所有的貸款全部還掉。當然再困難,當時的第一個要務,就是先讓孩子把大學讀完。
在房子重建過程當中住哪裡呢?埔里有二十戶的委員慈誠房子倒了,上人就在當時南投埔里聯絡處旁建了二十間的小木屋。那個小木屋只有十二坪半,住是很好,但是因為我們種田的必須有很多農機、很多機器,還有包裝的倉庫,很多東西沒地方放;所以我必須思索要在很快的時間裡把房子重建起來。
於是,我趕緊找建商,積極找政府的貸款。感謝政府有先給災民一百五十萬的免息,只要建屋契約簽了,開始動工就可以先領出來,但是還必須趕快再去找第一期建屋金。好比說,建房子的第一期金要五十萬,那個時候已經手中空空了,沒有五十萬,建商就不可能來動工;沒有辦法動工,就沒有辦法去借那一百五十萬,很多受災戶就卡在這個地方而無法重建。
我甘願損失也要把以前的保險積蓄全部都拿出來,就是用在重建的第一期金。我也感恩很多親戚朋友,有些受災比較少的或者家裡還有一點錢的,他們也信任我,先把錢借給我。所以我在地震那一年,農曆過年前三天就動工了,過完年就開始重建。到2001年的清明節,我就離開了組合屋,回到我們自己的房子。在組合屋總共住了一年半,就回去了。就是這樣,我們一家可以繼續走到今天。
經歷無常 一切夠用就好
如果不經過九二一地震,我可能會用比較貢高的心態,我是一個很善良的人,自己在做善事,然後自己做得很高興。但是沒有辦法看到「無常」,沒有想到災難會降臨到頭上來;因為沒有遇過,所以做慈濟就會有「做歡喜,卻沒甘願」的心態。
當一個人很認真去看待自己生命中無常的時候,才知道人沒有多厲害!我曾想過,九二一那天晚上,我家的女兒牆如果壓下來,現在這一些都不用談了。因此當面臨一個大災難卻沒有死,躲過了災難以後,第一個心境就是「把生命看得比較淡」。所以,九二一之後,我沒有很認真地去賺錢,因為我認為「夠用就好了」。
以前的我,夠努力!夠節儉!夠會買房子!但是不到兩分鐘,全部都沒了。佛典上說「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念起經來很好聽,但是無法體會。九二一以後才看清人多麼渺小,天地不可逆,這樣對生命比較豁達,要求比較少。
地震以後,我整個生活態度都變了,我跟我太太對於生命的要求、對於生活的要求,減低了非常多。從那時候到現在,很少買衣服,舊有的也可以穿得很好。另外就是對於做志工的態度反而更積極,因為我們知道今天不做,哪一天死了,就都不用講了。就如上人講的,會更積極地「把握機會,能做就是福」。
以前我會認為自己多麼偉大,我們都沒有為自己著想,都去幫助別人。但是經過大災難以後,才看清了:原來我們付出,收穫最多的是自己。帶著這些觀念,一路走過來以後,很多人問我說:「做慈濟做了那麼多年,你有什麼感想?」我只能說:「我沒有感想!我把它內化成為——那本來就是我該做的,我能做的,所以我歡喜地做,沒有其他感想。」
十年前(2009年)慈濟三義茶園的茶樹種植面臨瓶頸,上人希望我全心來照顧茶園時,我勇敢承擔起來。我一輩子做農,但我對種茶完全外行,我苦思要如何回報上人的託付,把那片土地照顧好,把慈濟精神帶進三義,把制度建立起來。雖然擔心自己能力不足,但只要想起九二一時,上人陪著弟子默默地吃那碗「師公飯」,我就告訴自己,再艱苦也要「甘願」承擔[13]。把茶園顧好,完成上人的囑咐,讓茶園成為靜思的後盾,也是我今生永不回頭的路。
[1] 佃農,需依照約定比例繳佃租給地主。
[2] 愛蘭橋,是埔里鎮進出中潭公路的主要通道。
[3] 1999年8月17日,土耳其發生芮氏規模7.4強震,造成嚴重傷亡。此訊傳至臺灣,證嚴上人深感難過與不捨,遂指示正在科索沃勘察的慈濟四人勘災團,就近趕往土耳其勘災;並呼籲「愛心動起來——馳援土耳其,情牽苦難人」,9月4日全球慈濟人紛紛響應,展開街頭募款活動。資料來源:2018年12月6日,慈濟全球資訊網〈慈濟在土耳其〉,http://www.tzuchi.org.tw/慈濟文史專區/國家地區簡史/item/22149-慈濟在土耳其(2020年3月11日檢索)。
[4] 陳忠厚承擔慈濟「中區慈誠大隊」第八中隊長;第八中隊包含埔里、草屯、南投、竹山、芬園一帶,當時慈誠中隊員有一百二十餘人;草屯的簡棋煌承擔該中隊的副隊長。
[5] 軍功橋,南投市對外交通樞紐,係中興路聯繫縣府、公所、南投地方法院、地檢署等機關進出要道。資料來源:2017年3月21日《自由時報》〈南投市對外交通樞紐軍功橋 重建提早完工〉,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11855(2020年3月11日檢索)。
[6] 上達下宏法師是很多資深委員口中的「宏師父」、「臺中師父」,因為認同證嚴法師慈悲濟世的理念,在慈濟草創初期,即以同道情誼開始幫忙慈濟,從勸募、慈善訪貧開始,帶動了一批精進的委員;中區很多資深的慈濟委員,都是由宏師父親自調教出來的。2013年9月19日,宏師父於南投縣魚池鄉「寂照蘭若」圓寂。資料來源:2013年9月28日,慈濟全球資訊網〈追思宏師父 各界法師送別〉,http://www.tzuchi.org.tw/全球志業/臺灣/item/10404-追思宏師父-各界法師送別(2020年3月11日檢索)。
[7] 上體下通法師,財團法人佛香書苑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8] 證嚴上人行腳出外,常以「醬油炒飯」簡餐果腹。後來某位委員的孩子希望媽媽也能節省金錢去濟助別人,便要求媽媽同樣用醬油炒飯給他吃;省下來的錢,就捐給師公(證嚴上人)做救人的工作。這個孩子便稱這種醬油炒飯為「師公飯」。
[9] 南投埔里信義路的地蓋埔里大愛一村,建有三百二十戶。資料來源:慈濟全球資訊網〈回顧‧921大地震〉,http://tw.tzuchi.org/921/pdf/921-31web.pdf(2019年10月6日檢索)。
[10] 中正一路100號埔里聯絡處旁,建有二十戶木屋,提供慈濟志工全倒戶住。資料來源:慈濟全球資訊網〈回顧‧921大地震〉,http://tw.tzuchi.org/921/pdf/921-31web.pdf(2019年10月6日檢索)。
[11] 「住屋全毀(全倒)、半毀(半倒)」認定體系與認定標準(簡稱「住屋全半倒認定」),以及「震災後建築物損害程度及其使用等級」評定作業、評估人員組訓與動員(簡稱「建築物安全評估」)等,在921大地震就已經建立。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都是全半倒惹的禍〉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newpdf/ST023.html(2020年3月11日檢索)。
[12] 依據民國89年9月20日財政部臺財融字第89286963號函〈九二一震災金融機構協議承受受災戶房屋貸款建物及其土地部分作業要點〉。資料來源:金融法規全文檢索查詢系統【相關實務見解】,https://law.banking.gov.tw/Chi/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cnt=14&sdate=20000901&edate=20000931&recordNo=4(2020年3月11日檢索)。
[13] 資料來源:《慈濟月刊》第574期〈甘願承擔 陳忠厚在靜思茶園〉,撰文/邱如蓮。